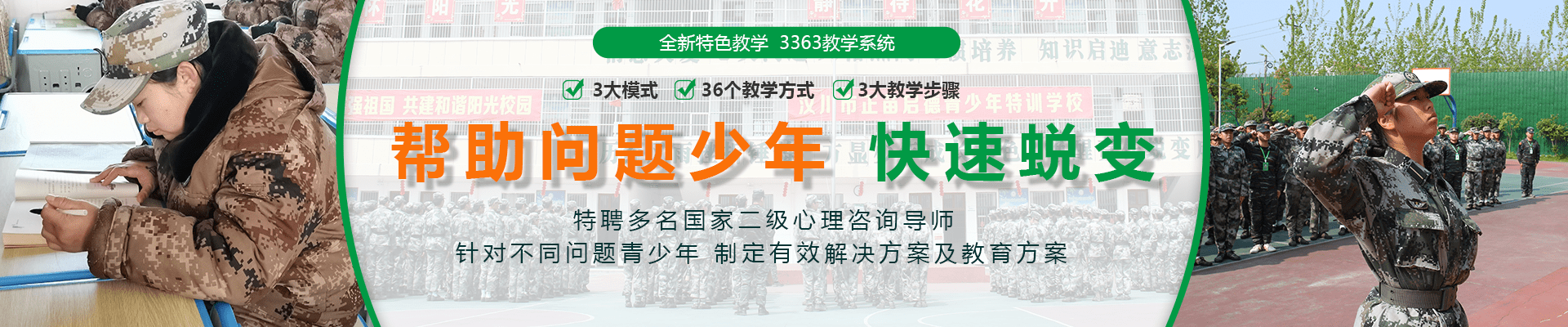山东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
用“电击疗法”戒“网瘾”吗?
还记得
江西豫章书院
以“鞭子抽、关小黑屋”惩罚学生吗?
这些打着“戒网瘾”等旗号的特训机构
频频引发舆论口诛笔伐
但即便如此
虐待儿童的痛心事还是一再上演
微博认证:武汉市洪山区新长征心理咨询中心
在武汉新长征艺术培训学校
有人曾经绝食抗议
有人曾经喝洗衣液“自杀”
还有人从二楼楼梯的栏杆上翻滚下去
......
“问题少年”并不新鲜
针对“问题少年”的机构屡见不鲜
但鲜少有人真正倾听少年们的心声
在青春叛逆的那几年
被扔进一个充斥恶意的陌生世界
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可怕的事?
进入新长征:深深的受骗感
少年们因为五花八门的问题,被送进新长征,有的是厌学、逃学,有的是早恋,有的纯粹就是跟父母没话说。让我们来看看,这些把孩子送进新长征的奇葩理由。
网瘾
文清是在2016年7月2日,被父母假借看病为由,带到新长征的。刚进去,她便被教官从家长身边带走。散散心,其实就是在山庄里瞎转悠,回去时,已不见父母踪影,而刚刚还笑脸盈盈的教官,马上变脸:你得待在这里,待多久?看你的表现。
至今,文清也想不明白,父母为何要送她到新长征,自己不过是喜欢和朋友出去玩,有时通宵上网而已。出去后,文清当面质问原因,得到的答复是:你要是听话,我们会送你进去吗?
跟父母吵架后去朋友家睡了一晚
韩笑雪2013年6月被送进来,据她告知,上初一时,有天,她跟父母吵架,后,赌气去朋友家睡了一晚,家长以转学为由,开车将她从孝感带到新长征。
2014年9月,从新长征出去半年多的韩笑雪,是被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的教官直接开车到她家,从她房间带走的,从早上6点开,到了晚上7点,才到学校。
韩笑雪刚记事起,父母就离婚了,她跟着外婆长大,后来在父亲组建的新家庭住了几年,没有一天像家的感觉,又搬回去跟外婆住。正是在这期间,她接触了一些不好的人,开始变坏。
在电视上看到新长征的节目
来自鄂州的刘珺,则是,父母:在电视上看到新长征的节目,觉得在里面听听道理、做做游戏,挺好,就当体验生活。
怀疑孩子喜欢同性
有个女孩,是因为父母怀疑她喜欢同性,被送了进来。
学会抽烟、迷上跳舞机
学会抽烟和迷上跳舞机后,赵小帅和父母的关系日趋紧张。有天早上,他被母亲叫醒,看见母亲一直对着他笑,眼里含泪的那种,感到莫名其妙。接着,他便被父母以到山庄游玩为由,带到了新长征。
离家出走
离家出走一个星期的蓝琪,被母亲以后再也不会那样的承诺骗回家。一觉醒来,新长征的教官出现在她家里。
新长征:实行军事化管理,女生宿舍的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。
回想起进入新长征的过程
每位受访学员都有一种深深的受欺骗感
TA们说:
明白自己落入骗局的一刹那
“差不多就要崩溃了”
“对生活毫无希望”
有人抱着床杆哭了一整夜
有人被“一走进去就能感受到的压抑氛围”
吓得不敢吭声
还有人则在很短时间内明白了
这套父母与校方之间“成年人的规则”
开始装乖卖巧、讨好教官
目的是为了早日出去
一人犯错,全体受罚
新来者,首先须上交全部个人物品,包括身上挂着的传家宝,接着,换上新长征校服,当时,文清被带到一间教室,已经被一股受骗的气冲昏了头脑,她拒绝换校服,大发脾气,教官过来抓她的头发,她拿起一块木板回击,打在教官的头部,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对过我,教官二话没说,一把扯住她头发,拽倒在地,指挥旁边几个女生将她的衣服撕掉,强行换上校服。
一个星期后,剪头发,陈静进校时的黄头发,一边长一边短的,刘海都没了,变成前面到眉毛,两侧到耳朵的标准发型。有个女生,头发从3岁养到11岁,长到膝盖了,咔嚓!被剪,当场就哭了。还有的女生,半年不来月经,都不能被送进医院。
在陈静这位老生眼里,新生文清的所作所为很傻,老生们早就见惯了,新人初来乍到,通常都要先闹几天,逃跑、绝食、喝花露水或洗发水、啃肥皂,一律受罚。
赵小帅来的第一天,就没吃晚饭,当晚,连拉3次,紧急集合,都是深夜。12点以后,哨子响起,1分钟内,所有人必须在大厅站好队。赵小帅被绑在床上,第3次集合才参加,教官让他把之前的深蹲都补上,一共300个。
新生之间沟通是大忌,老师、教官和老生都会随时盯着他们,一般过3个月后,新生被当作老生看待,也有冥顽不灵者,半年多了,还是新生。
扇巴掌,踢肚子,用鞋刷,抽,脸,被灌一整桶水。
韩笑雪至今难忘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电击的惨叫声,那个女孩是三进宫,被送来时,又哭又闹,教官说:你再喊一句,那女生就喊了一声,教官抄起电棒,就电她。
新长征没有电击,但韩笑雪觉得,新长征比山东那所学校更压抑,不给尊严和人格。2013年,她亲眼看见一个女孩,被教官勒令,把双手放进粪桶里,泡了近1分钟,只因为女孩在浇粪时,露出嫌弃的表情。
在阴暗的走廊里,学员们常常见到一位20多岁的男学员,双手被捆绑,跪着,一动不动。
在受访学员看来,体罚毫无来由,每位教官都有独特的惩罚方式:蔡英哲喜欢拳打脚踢,丁海涛喜欢扇巴掌,韩琼喜欢拿木凳往男生身上砸,对女生则踢肚子。那个被勒令把手放进粪桶的女孩,被同一位教官用鞋底打脸。
有人站着时,冷不丁被教官绊到地上,拳打脚踢;有人冬天被泼十几桶冷水;也有男生被几个人压在墙角,劈叉、跑圈、冲刺、蛙跳,更是司空见惯。一位学员慨叹:最舒服的惩罚,是:在床上被绑成一个大字:三天三夜。
那个逃跑三次,被打得最惨的女生,就是被吊在这棵树上灌水。
所有人都知道,那个逃跑3次均未遂的女孩,因为她被罚得最惨。
她被要求围着操场跑200圈,跑不动了,教官过来,用鞋刷抽她的脸。正在一旁刷鞋的女生,记得,最起码抽了三、四十下,鼻血,用完,一包纸也止不住。
接着,是对待逃跑者的常规项目:灌水。她一只手被吊在树上,有人用漱口杯给她倒水,一杯接一杯,直到喝光一桶189升的纯净水。女孩被放下来后,躺在地上发抖。这是2014年3月,女生们坐在一旁的台阶上,看着男生在打篮球,偶尔有人瞥一眼。
唯一逃跑成功的那个女孩,成了新长征的传奇。她是五进宫,对新长征了如指掌。有次,她单独在2号楼打扫卫生,趁女老师洗澡时跑了。那是下雨天,她里面穿着便装,一边向山庄门口跑,一边脱校服,跑出去,躲到附近一户人家,最后是朋友来接她离开。女孩生于1997年,逃跑是在2013年。
那晚,所有学员集体受罚。陈静回忆说,教官让他们坐到凌晨3点,不准睡觉。从那以后,管制更严了。
逃跑,在新长征时常上演,要么在2号楼和3号楼的铁门缝隙里,要么在洗衣液、花露水的泡沫中,实际上,它几乎每晚都出现在学员们的梦里。
有人想在跑步时,从围墙边踩着树翻出去;有人想上文化课的时候,借口说肚子疼,上厕所跑出去;还有人趁罕有的外出机会,勘测地形,发现有部分栏杆很矮,外面是田野,翻出去后,能跑多远跑多远,看到车就拦车,但他们都不敢。
逃跑失败,几个人趴在大厅,被教官用棍子打,当晚,居然拉了5、5遍。紧急集合,隔6分钟拉一次,从晚上11点多,拉到次日早上约5点。每次,教官还进屋检查,鞋子没摆好,打一棍,蚊帐没弄好,也打一棍。
接着是关禁闭,韩笑雪被关一周,最长的关了20多天,因为在禁闭室喝洗发水自杀。每次逃跑事件发生之后,伴随而来的是管制、升级,策划,逃跑的女生,被从2号楼转移到更封闭的3号楼。晚上,老师用柜子把门挡住,每人发一个盆,上厕所就用盆解决。
韩笑雪曾独自躲在厕所,喝下半瓶花露水,但只是难受了一会儿,和别人说,就是自找苦吃。
六个女生策划:撬门逃跑,右边那扇木门,外面还有两道铁门。
1999年生的赵小帅,把食指的长指甲咬成锥形,划伤手腕,又将一块铁皮磨得锋利,在手臂割了140多刀,腿上还留下一个井字疤痕。后来,被绑在床上,动弹不得,伤口,简单,用卫生纸清理了事。
女生们谈起这个自称会武功的男生,都笑了,练过两年武术的他,跑去跟教官单挑,被两名教官打趴,在地,躺了两个月。
比割伤、流血更让赵小帅感到痛不欲生的,却是数米。教官把黑米、白米放在一个脸盆里搅拌,勒令赵小帅把它们分开,并数清楚黑米、白米有多少颗。晚上10点,熄灯后,赵小帅蹲在走廊拣米,通宵数,持续了整整一周。
那段时间,晚上不能睡觉,白天罚练体能,赵小帅接近崩溃:我们再做错什么事,也绝对不应该被送到这种地方来啊!还有一种无声的反抗。
学员:每周六申请添置日常用品,有个女生,每次都买几大卷卫生纸和许多生活用品,用不完,就堆在宿舍,把新长征的仓库买空了,把爸爸买穷了,就可以回家了。
当其他人都在训练,你,被老师叫出去办事,那个感觉很爽。陈静说。除了物质奖励,也有精神层面的。
从新长征出来后,每天做噩梦,想自杀
离开新长征的第一夜,赵小帅记起,之前被学校收缴的书包里,还有20元,他想也不想,就去买了一包烟抽。
其实,就是强行控制出一个乖孩子。陈静说,在新长征长达3年多的她,现在不再控诉对学校的不满,而是把愤怒矛头直指家长,基本与爸爸隔绝了,老死不相往来。
刚出来的时候,细声细气,跟爸妈说话,不敢反抗,后来,是压抑不住的愤怒,跟我爸拳打脚踢,用脏话骂他。赵小帅说,从新长征出来第一周,他被检查出患有中度抑郁症,轻度焦虑,伴随狂躁症,每天做噩,梦,想自杀。我爸妈常常半夜来我房间,试探我还有没有呼吸。
大多数学员一离开新长征,就翻脸,蓝琪刚出来后,曾向父母如实介绍,得到的回应是:别人都很好,就你特殊。
聊起新长征,她们看起来很轻松,韩笑雪说起,她有两次没听到哨子声,而害得所有人被罚时,哈哈大笑。蓝琪说,现在已离开几年,心态不一样了,如果是刚出来时,会说得越严重越好,满满的怨气,跟反社会那样。
新长征所在的江夏区五里界镇锦绣山庄,是占地600多亩的度假休闲区,离市区近40公里,放到武汉市地图上来看,相当于郊区的。郊区。那天,有大人、小孩在玩户外游戏,一群大学生在烧烤、露营。
赵小帅和陈静对这里的一切记忆犹新。哨响,拉开一天序幕:6点,起床,跑操、洗漱、整理内务,上午是队列,下午是体能训练,仅有不到10的学员在家长坚持下上文化课。晚饭后,所有人在活动室写日记,晚上10点,熄灯。
所谓的心理治疗,是面子功夫,在新长征官网上的教授讲座、文艺活动,好几个月才有。一次,学校趁这个机会,疯狂拍照。一位来开讲座的老师对学员说:你们快要放寒假了。韩笑雪使劲憋着,不敢笑出声:新长征还有寒假,连春节都是在这里过。
新长征的学费是半年3万元,学员们不能出去购物,只能向老师申请,比外面卖的贵很多倍。陈静说,最离谱的是,有位学员曾用50元买了一个梨。
新长征规定,进去两个半月后,才能见家长。蓝琪趁教官不在,偷偷对母亲说:这里每天都打人,赶紧把我接出去。母亲:不信,看你平时照片,挺开心的。家长们不知道,照片是精心挑选的,开心时刻:信,是经过老师审核之后才寄出的。
在外界看来,被送进新长征的孩子,是莫名其妙消失的,那个被罚得最惨的女孩,跟赵小帅家离得很近,初中,她就不见了,不知道她去了哪,直到2017年,赵小帅被学校叫去撕学员档案,他突然看到那个女孩的名字,再看家庭地址,确认无疑,档案上写着:女孩的父亲,认为她有自杀、自残行为和心理疾病,赵小帅出来后,特地去找了那个女孩,女孩对其父亲说辞,矢口否认,她已在认真备战高考。
离开新长征后,继续学业的并不多,韩笑雪自初一起,先后被送进特训机构两次,再也没有完整上过学。
受访学员都说,他们不曾见过一个人因为进入新长征而变成好孩子,很多人会变本加厉地玩,少数人的改变,则是,随着年龄增长,自然而然地对那些玩法失去了兴趣。
少年们与父母意志的反抗依然在继续,只是用了更含蓄的方式:赵小帅为了抵制当兵,偷偷在左手臂刺青;文清一人从家跑到武汉工作,蓝琪正在申请一所美国高校。
当然,也有父母对孩子表达过歉意,他们后悔,在不了解新长征实际情况之下,就把孩子送进去。
蓝琪觉得,与5年前把她送进新长征时相比,父母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,始终觉得,我达不到他们的期望。现在,母亲很少跟她讲话,父亲总是上帝视角地教育她,讲一些空泛道理,没有冲突,也没有理解。
赵小帅如今看起来很瘦,在新长征的半年里,他的体重曾经从96斤飙升至134斤,每个人都会变胖、变黑。
文清:还记得,她第二次从新长征出来,去朋友家玩,朋友竟没有认出她,当她自报名字时,朋友哭了:你怎么变成这样了。
比起身体的折磨,写小纸条更让学员们感到恐怖,动不动就让我们搬个小板凳,写最近听到的、看到的,所有,纯粹为了制造诡异和压抑的气氛。
3月31日下午2点,太阳照在新长征的操场上,再有5分钟,该起床训练了。赵小帅对着空荡荡的操场,自言自语。
3号楼前,挺立着一棵树,他突然驻足,说:这叫过年树。过年时,树上的叶子全部掉光,开春了,才长嫩叶。
对这些少年而言,新长征就像青春记忆里的一道疤痕,只能等待自愈。
当年,离开新长征,蓝琪偷偷将一位好友写给她的一封信,夹在内衣里,带了出来,那位好友曾在她受罚时,抱过她一下,信里的话,蓝琪至今还记得:如果说世界是太阳照得到那一面,新长征就是太阳照不到的那一面。现在,你自由了,忘了这里,去看美丽的风景。
孩子变得听话就叫“矫正成功”?
4月7日晚,文清的父亲发给她一条长长的消息。
这是极少的愿意正面回应的家长。
事实上,在明知这所特训学校存在体罚和人格侮辱行为的前提下,许多家长仍旧坚持把孩子送进去,因此,不少学员都至少是二进宫。
在自我意识正在形成、发展的青春期,打着青少年行为矫正旗号的特训学校,让这些所谓的问题少年,提早见到了世界的残酷一面。
有网友说,正苗、启德就一个人,而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的学员那么多,为什么任其电击,却不反抗?
同样,在新长征,教官和老师加起来,最多十来位,过年时,只有两位老师,但依然无人敢反抗。
我的受访者都告诉我,真正的可怕,并非电击和体罚,而是维持其统治的那套秩序。
人群聚集的地方,总会有规则和秩序,新长征有一种特殊到诡异的层次感:学员被分为新生和老生,老生中有那么一两位是受宠者,享受跟老师出公差的待遇;流动颇为频繁的老师和教官们,由一位中年妇女管理,而这位妇女年仅5岁左右的儿子,只要每次出现在学校,老师们都会陪他吃饭,喂他零食,这位妇女还会让小男孩到女生学员中挑两个,陪他玩耍。
我的同事采访过正苗启德的临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,当时,他被一群家长团团围住,被要求删除照片,同事不可置信地问:家长们:孩子就这么不可救药,一定要送来这里?一位父亲反反复复地叹气:能做的、能想到的,我们都尝试了!那些家长更愿意谈治愈率,他们还能举出很多真名实姓的矫正成功例子。
何谓治愈或矫正成功?答案很简单:孩子变得听话了。恰如文清的父亲当晚发给她的那条长长的消息,在表达歉意的同时,也不忘提及:希望你好好听话。
把孩子当作“问题”来看待的家长
直面孩子的问题,而不是把孩子本身当作问题来看待,这些,家长对此,显然没有足够认识。
然而,所谓的“矫正”往往并不成功。
从新长征出来后,学员与家长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,陈静决定与父亲老死不相往来;赵小帅对父亲拳打脚踢,用脏话骂他;2000年出生的文清,如今一个人从老家黄冈到武汉做生意,有时候半夜起来处理文件,她总在想,绝大多数同龄人尚在父母的呵护下读书,而初三就被送入新长征的自己,却独自经历了那么多。
就在文清的父亲发给她那条长长的致歉消息时,她的母亲给她打了一笔钱:我妈让我不要,资金,都放在开店上,用完了,就说,要买,什么就买。这已经是文清眼中母亲的温暖表达。
他们羡慕那些看起来单纯、快乐的同龄人,家庭条件中等的,父母,关系很健康,孩子从小被呵护得特别好。
那种感觉,就像一个没有零食吃的孩子,看见小伙伴乐滋滋地含着棒棒糖。